
來源:深圳市文聯
時間:2022-0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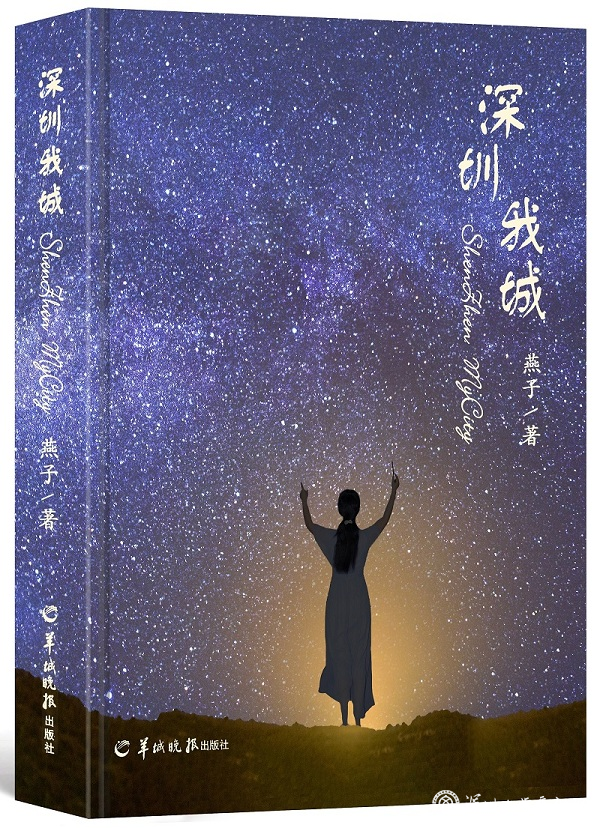
《深圳我城》書影 / 資料圖
深圳,在世人的眼中是一座“引潮流之先”的先鋒城市,也是一座光怪陸離、讓人捉摸不透的新興城市。它怎樣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為現代化國際化大都會,人們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解讀。文學作品中的深圳,更是多姿多彩、異彩紛呈。尤其是作為文學“快槍手”的報告文學,對深圳的表現和描述,更是形象可感,發人深思。燕子的報告文學集《深圳我城》,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它撿拾深圳城市變遷的“雪泥鴻爪”,珍藏深圳“社會生活的生動細節”,構成了深圳城市“記憶的一部分”,堪稱深圳城市變遷的形象寫照,起到了立此存照的藝術效果。
率先領跑,貿通天下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經濟特區和外向型開放城市,最早顯示領先示范效應的是快速發展的外貿。《深圳我城》的作者敏銳地看準了這一點,對此進行了形象而又生動的表現。
寫于 2020 年的《貿通天下》是這本報告文學集的首篇。作者開篇就按時間遞進對深圳貿易在全國的地位進行了明確界定 :“1992 年,深圳進出口貿易總額首次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一位……2012 年 , 深圳外貿出口實現全國‘20 連冠’,領先地位十分穩固 ;2019 年 , 深圳外貿出口連續 27 年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 , 實現‘27 連冠’。”顯然,作者是用這種先聲奪人的手法,讓讀者對深圳外貿的領先地位留下深刻印象。然后,拋出讀者必然要問的問題 :“在中國經貿乃至世界經貿舞臺上領跑,深圳憑什么能做到?動力緣何?‘秘訣’何在?”這些引人入勝的問題,為后面的敘述進行了很好的鋪墊。
在作者的筆下,深圳的外貿幾乎是從集體無意識開始的。從根本不懂什么是外貿,“什么能賺到外匯,就搞什么”,到“一家大細穿膠花”的家庭作坊零敲碎打,再到主動約香港老板過境面談,決定引資辦廠,逐漸形成創辦外貿生產基地、開展邊境小額貿易、發展“三來一補”的新局面,硬是把外貿做得像模像樣。作者在敘述這些故事的同時,恰到好處地進行抒情和點評,彰顯深圳外貿從無到有逐步發展的創新意義。作者深情地寫道 :“新時期發韌于深圳經濟特區的對外貿易,猶如陌上小草,執意破芽生長。”“如果說家庭作坊式的‘三來一補’是民間在政府的庇護下有意無意將中國緊閉的大門試探性地推開一條縫隙的話,那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進行探索和創新的改革開放,則是決然砸開鐵鎖,將門越開越大。”由此,作者把深圳外貿的發端和壯大,提升到改革開放、打開國門的思想理論高度,使“貿通天下”名副其實,形象可感。
作者把華強北“中國電子第一街”、華為公司的崛起、大疆無人機等作為深圳外貿與科技創新相互融合的范例,以一個個驚心動魄、扣人心弦的故事,反映出深圳外貿發展和科技創新相融合的“艱難輝煌”,讓讀者清晰地感受到,“無數關于外貿、關于財富、關于人生命運的傳說從華強北擴散,在深圳這座城市、在國內乃至海外流傳”;深刻地認識到,從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喊出“10 年之后,世界通訊制造業三分天下,必有華為一席”的豪言壯語,到華為形成全球頂級品牌,真正做到了“把數字世界帶入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組織”,“讓云無處不在,讓智能無所不及”。作者在敘述這些故事時,始終伴隨著理性的思考。在她的筆下,華為誕生于深圳“這片擁有創新之魂的土地,先天就帶有創新的基因,后天更以創新為圭臬”。華為的創新是區別于低層面“自主創新”的“開放式創新”,“在華為的創新實踐里,如果沒有‘開放’和‘全球’這樣的關鍵詞,那么,在‘自主創新’意義上的成功也許將不復存在”。而大疆則是“用一流的產品重塑了‘中國制造’的內涵”,“占據了世界無人機市場的主導地位”,“具有行業的領先優勢和全球影響力”。作為一個作家,敘事和描述能達到這樣的思想理論高度,實屬難能可貴。

深圳科技園 / 資料圖
科技創新,破繭而出
如今的深圳,是全國公認的科技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一面旗幟,可深圳科技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是怎樣破繭而出、做強做大的,許多人并不了解。為此,作者特地采寫了《破繭而出》。在這篇寫于 90 年代的報告文學中,作者通過描述張小云、孟龍、齊翠珍、楊宇全、鄭寶用、李一男等一批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生動地反映出深圳科技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從上個世紀 90 年代破繭而出、艱難起步的發展歷程。
張小云是 80 年代從中國科技大學來到深圳的一名生物學家。深厚的家學淵源和在美國做過訪問學者的學術底氣,使她懷著大干一番的宏圖壯志來到深圳大學。可她到了深圳后發現“深圳并不是搞科研的樂園”,“什么氣氛都有,就是沒有科研氣氛”。她想辦生物專業,可是沒有學生報考 ;她創辦了“深圳大學生命科學研究室”,研制出了“愛爾液”“賓健歸”等消毒液,可她不懂市場運作,也沒有人給她保護知識產權,只好被無良商人欺騙和利用,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科研成果的經濟效益被別人侵占和掠奪。面對這種十分不利的科研生態,張小云沒有氣餒,更沒有放棄。她憑著一個科學家的志向和情懷,堅持在困境中搞科學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科研論文,推出了一個又一個科研成果,有些科研成果甚至是國際首創,產生了較大的國際影響。更為可貴的是,她還帶頭做科普講座,為深圳營造科研氛圍。她的“生命之樹結滿秋天的果實”,以一己之力為深圳的科技創新破繭探路。
如果說張小云反映出深圳早期科技創新的艱難和科研人員的執著,那么,孟龍、齊翠珍等科技工作者的經歷,則體現出科研人員不無悲壯的科研探索和為國奉獻的精神情懷,各有鮮明特色和象征意義。
孟龍懷著“探索一個新的、公平的、能充分調動個人積極性的科技單位管理模式”的夢想,從上海來到深圳,擔任深圳羅湖工業研究所所長,力圖“完成從純學者到學者兼商人或學者兼總經理的‘美麗而輝煌’的轉變”,“提出了以高新技術為目標,以市場為導向,實現技術開發和經濟效益良性循環的經營方針”,可在實踐操作中卻常常因缺乏資金而一籌莫展。“手中握有很具市場價值的科技成果,卻因缺乏資金而難以推廣。”“根本無法完成產業化商品化的過程。”其中的辛酸和無奈可以想象。這也正反映出深圳科技創新起步的艱難。
齊翠珍是深圳科技工業園長園公司的總工程師,她“毅然決然地走出象牙塔,走出困惑,在科研和市場的裂谷上艱難地構建銜接兩者的橋梁”,成為“中國熱縮材料應用的先驅之一,開辟了這類產品在中國市場上的大規模應用”,并在國際競爭中讓經銷同類作品的“美國瑞侃姆公司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非常痛惜的是,她終因辛勞過度而英年早逝,年僅 49 歲就因心臟病發作而離開了人世。她留下的那句“只有中國人愛中國,中國才有希望”的真情話語,印證了她為深圳科研創新和國家科技發展而無私奉獻的赤子情懷,成為中國一代科技工作者的精神象征。
寶安電子研究所所長楊宇全,以“中國人不比日本人笨”的自信和頑強,“設計出一種空調微處理器掩膜”,迫使日本人退出美的空調集成電路的競爭,以創新成果證明了他自己的豪言壯語 :“不能把失敗歸于環境,不能坐等環境好了再干。我們必須利用有限的空間和資源去做最大的努力,創造和實現自身的價值。”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副總裁兼中央研究部總裁鄭寶用,和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程控技術部經理李一南,都是 30 歲以下的科技少壯派。他們“從學校到學校然后一步跨入華為”,“沒有坎坷的經歷和太多的挫折”,“趕上了可以大顯身手的好時代”。他們審時度勢,奮發有為,“每天干十幾小時的活,碰到難題,想破腦袋也要鉆下去”,支撐他們的“不是‘沒有意思’的頹喪萎靡,而是精忠報國的激越昂揚”,“他們完全有能力托起‘中國明日的太陽’”。華為的成功有他們的一份功勞,深圳科技創新的快速發展離不開他們的貢獻和付出。
作者精心描述以上幾位科技工作者,決不僅僅是為了給我們講故事,而是通過鮮活的個人和生動的事例,全方位、立體性地展現深圳科技創新破繭而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逐步推進的歷史進程。從時間跨度看,兩代科技工作者面臨不同的環境、條件和機遇。前一代人的艱難探索為后一代人的大有可為創造了必不可少的外在條件。從內涵變化看,從資金缺乏、與市場脫節、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護,到政府制定法規、明確政策、資金扶持、知識產權保護,經歷了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作者匠心獨運,把科技工作者的個人經歷,與社會變革、城市變遷、科技創新發展聯系在一起,以小見大,由點及面,讓讀者真切地感受到科技工作者為推進深圳科技創新發展“不爭待遇、不計報酬、甘于寂寞、甘于淡泊、樂于奉獻”的精神風貌,全面地了解到深圳科技創新發展從“沒有科研氛圍”到“高捧科技”的變化進程。一篇報告文學能有如此大的文化容量和意義內涵,已足見作者的見識和功力。

深圳世界之窗 / 資料圖
地上地下,煥然一新
深圳作為開放型的移民城市,在發展進程中有兩個突出問題。一是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人口不斷增加,城市的容量越來越大,基礎設施不能滿足需要,交通堵塞成為影響民生的大問題 ;二是外來人員的涌入和管理應接不暇,“城中部落”和“三無人員”嚴重影響市容市貌和城市管理,成為令人憂心的“城市癰疽”。不解決這兩個突出問題,深圳很難成為百姓滿意、形象良好的現代化城市。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這兩個問題終于得到圓滿解決。《深圳我城》中的《地下,又一座城市在成長》和《懸浮的世界》這兩篇,形象地記錄和反映了深圳通過建造地鐵和清理“三無人員”解決這兩個突出問題的全過程。市民拍手歡迎這種大動作帶來的新變化,稱之為“地上地下,煥然一新”。
眾所周知,緩解城市交通堵塞的最好辦法是建造地鐵。然而,在深圳這樣的新興海濱城市修建地鐵,困難之大和問題之多,幾乎難以想象。但深圳硬是以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把政府和市民的“地鐵夢”變成美好的現實,在地下建起了一座新城,“托起了城市的新高度”。
作者在描述深圳建造地下新城的奇跡時,仍采用先聲奪人的手法,以一系列數據和硬指標,展現出深圳地鐵從無到有、領先全國的壯麗風貌 :1989 年,深圳提出建造地鐵的動議,并很快成為政府決策,構建了一個在當時不被看好的“地鐵夢”;1998 年5 月,借香港回歸祖國的契機,國家計委批準深圳地鐵工程立項,命名為“深圳地鐵一期工程”;2004年 12 月 28 日,深圳地鐵 1 號線正式開通,深圳進入“地鐵時代”。
后來,“深圳地鐵版圖一變再變,一擴再擴”,“地鐵里程每過幾年就會以倍數增長”,地鐵密度“列入世界頂尖水平”,被評為國內“地鐵最便捷城市”。
在作者的筆下,深圳實現“地鐵夢”的過程,融注著攻尖克難、改革創新的奮斗精神。
經費不夠怎么辦?創造香港私營企業參與深圳基礎設施建設、向社會提供服務的“特許經營”新模式,最終實現“建造—營運—移交”的全過程 ;
施工難度大怎么辦?量身定制雙護盾 TBM、創造“拆橋神器”模塊車,讓這些“變形金剛”和“超級戰士”在地鐵施工中大發神威 ;
噪音擾民怎么辦?錯時施工,日夜兼程,“暗暗地挖”,把對市民生活的影響減少到最低度。
面對深圳地鐵建造的革新創造,作者深情地寫道 :“這不僅是技術創新與科技進步,更是‘綠色深圳’、‘綠色地鐵’理念的踐行。”“建設者努力讓‘城市中的工地’與環境相生相融,書寫出‘創新地鐵’、‘科技地鐵’、‘美麗地鐵’的動人篇章。”讀到這里,我們不禁要拍手稱贊 :“壯哉,深圳!壯哉,深圳地鐵!”
如果說,深圳建造地鐵是完善城市基礎設施、緩解交通堵塞的創舉,那么,深圳清理“三無”人員,則是強化城市管理、割掉“城市癰疽”的壯舉,使深圳真正走上了現代化城市的發展軌道。
作者在《懸浮的世界》中開宗明義 :“三無”人員的出現,是深圳特區早期改革開放的自然現象。“自從 1989 年中國黃土地開始躁動不安,大量剩余勞動力涌動著沖向城市,只有 327.5 平方公里的深圳特區便驟然感受到大軍壓迫的沉重。關內外大批開發區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的‘三資’企業,各類公司、工廠,無法消化源源不斷從北面風塵仆仆趕來的人群,不能被吸納又不愿往回走的人滯留下來,便成為游蕩的‘三無’人員。”
接著,作者理性地剖析“三無”人員對城市產生危害的客觀必然性 :“城市對于他們只是一種誘惑,一種改變窮困潦倒命運的可能。由于他們沒有長期的職業計劃,其作為大都是以掙錢為主要目的的短暫行為,因此具有一定的破壞性和掠奪性。”
深圳“三無”人員已達到較大的數量規模,其對城市的實際危害十分明顯。亂搭亂建“給現代化城市的面容染上了臟亂差的污點”,違法犯罪“在城市健康的肌體上滋生了黃賭毒黑盜劫的腫瘤”。作者深刻指出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假如任由一些人不講秩序地在深圳‘撈世界’,另外一些人的世界就會碰撞得支離破碎。‘三無’人員問題,關乎深圳的穩定和安寧,也關乎深圳的現代化和未來”,“必須面對,必須有所作為”。
《懸浮的世界》的副標題是 :深圳市 1994 年春清理“三無”人員備忘錄。作者除了以事實闡明“三無”人員形成的原因和產生的危害,更以數據表明深圳怎樣大刀闊斧、干脆利索地清理“三無”人員。僅在一個多月內,“全市共清理遣送‘三無’人員 23.1萬人,拆除山邊、路邊、水邊棚寮 6 萬余間,清查‘三無’人員駐足的工地、工棚、公共復雜場所、出租屋、個體店鋪等 10 萬余間,摧毀地下工廠 839間”。這些數據說明了深圳清理“三無”人員的力度和效果,也表明作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真正做到了“報告文學讓事實說話”。
尤為可貴的是,作者沒有情緒化地陶醉于深圳清理“三無”人員的成果,一味地給予贊美,而是進行了客觀冷靜的理性分析,提出了現代城市管理中一些發人深思的深層問題。作者寫道 :“清理‘三無’人員是一項內容龐雜、任務艱巨的系統工程,并非靠一個‘清’的高潮就可以一勞永逸。如何真正科學地管理好流動人口,對于深圳的社會發展和經濟繁榮至關重要,亦是擺在深圳面前一個積久年深急需解開的癥結”,“過死的限制和放縱的自由都會造成我們所不愿看到的后果”。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作者當年思考的問題,如今深圳已經妥善解決,城市管理已提高到一個全新的水平。
旅游新城,魅力深圳
深圳是改革開放中誕生的經濟特區,又是毗鄰香港的新興城市,從創辦特區那一天起,來深圳公干或旅游觀光的人就絡繹不絕。但是,人來了給他們看什么?怎樣讓他們覺得到深圳不虛此行?如何使深圳成為名副其實的旅游新城?這是擺在深圳面前的突出問題。作者在《魅力深圳》這一篇中,詳細回答了這些問題,反映出深圳由邊陲小鎮到旅游新城的發展變化過程。
作者的描述既形象又生動 :
早年的深圳,“唯一可游的大概就是只有兩只瘦猴亂蹦亂跳的小公園”,人們戲稱為“一個公園兩只猴,一位警察看兩頭”。1979 年深圳建市,國務院文件指示“把深圳建成旅游區”。1980 年,深圳特區創建,來深圳參觀考察的人,可去的地方只有“五湖四海”“一條街”。“五湖”是作為公園的西麗湖、香蜜湖、石巖湖、東湖、銀湖 ;“四海”也是公園,只是地處海濱,分別是蛇口、深圳灣、小梅沙、大亞灣 ;“一條街”是一街兩制的“中英街”。那時的深圳“還遠不是人們心目中的旅游城市”。
接下來,作者的描述更加富有詩意 :
“80 年代的最后一個冬天,深圳灣畔出現了一幅瑰麗的畫卷,像一根神奇的魔杖,把中國的名山大川、文化古跡全‘點’到一起來了,這就是‘錦繡中華’。它的出現,標志著深圳旅游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觀光旅游階段。”自此,“‘五湖四海’的格局被一舉打破,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等主題公園相繼出現,深圳旅游享譽國內外。”
如果說,以上的描述是作者對深圳旅游從無到有、快速發展的全景展現,那么,作者恰到好處的點評和抒情,則是對深圳成為旅游新城的熱情贊頌。作者深情地寫道 :“把祖國的秀麗河山、文化古跡搬到深圳,那該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在方圓數十萬平方米之地展示中華民族燦爛的歷史文化,讓人們一步邁進歷史,一日游遍中國,那該有多大的吸引力!由此圓一個‘讓世界了解中國’的夢,又是多么的有意義!”“如果說錦繡中華像一部凝固的中華史書,民俗文化村則像一臺濃抹重彩的大戲 ;如果說錦繡中華像一座薈萃中國名勝古跡的寶石庫,民俗文化村則像一首頌揚中華民族大團結的贊歌”;“從錦繡中華到民俗文化村,從歷史的懷想到民風的張揚,人們行走著的,是一條通往中華精神殿堂的、充滿鳥語花香的路徑”。“錦繡中華微縮景區、中國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三大景區融匯成一個‘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了解世界’的大型文化旅游區。其特色之鮮明,主題之完整,內涵之豐富,建設之精美,管理之先進,實力之雄厚,在中國人造景觀中獨樹一幟。”
上述富有詩意的描述和贊頌,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了深圳旅游業快速發展的脈絡和軌跡,看到了深圳旅游新城迅速崛起的奧秘。其核心是面向世界的寬廣視野和銳意創新的戰略思維,這是深圳特區的鮮明特色,也是作者妙筆生花的藝術魅力。
作者書寫這篇的標題是《魅力深圳》,但通篇寫的是旅游業的發展,其內核就是旅游賦予深圳魅力和活力。作者在表明這種內在邏輯關系時,有著非常精到的描寫。她把深圳旅游業所展現的魅力歸結于文化的魅力,體現為文化的精神內涵和形象的新穎別致。作為深圳本土作家,她不無自豪地寫道 :“每年,都有大批大批的人入廣,大批大批的人來到深圳,只因廣東的魅力,深圳的魅力。”“深圳從一片荒蕪至一片繁華,其間的歷史跨度,文明跨度,物質跨度與精神跨度,非親歷親見者不能想象其巨大。深圳神色自然態度從容地完成了這一跨度。”而深圳旅游業的快速發展顯然是完成這一跨度的重要體現。“人們在華僑城三大景觀看到的不僅是一種景物的簡單‘克隆’,給人最大享受的,是濃郁的文化氣氛和民族特色”,“文化滲透在旅游當中,這是一個成功的杰作”。
作者深刻地指出,“深圳旅游業并沒有因為華僑城人造景觀風頭正勁而忽略自然風光的開發”,而是“珍惜天然資源,開發自然風光風景區”,“構造出人造景觀與自然景觀兩大相依相重的板塊”。被譽為“世外桃園”和“牧歌田園”的仙湖植物園和“青青世界”等自然風景區,以及大鵬所城、赤灣少帝陵等歷史文化景區,就是生動的例證。它表明,深圳的旅游文化豐富多彩,深圳的旅游景觀新穎別致,博古通今。這種源自文化底蘊和文化創新的魅力,既有精神的感召力,又有形象的吸引力。因此,“深圳是富有魅力的,這魅力是人類才智的魅力,是創造活力的魅力,是深圳精神的魅力”。當我們讀到這里,情不自禁地要贊嘆作者對深圳魅力的準確把握和深層揭示。
文學是社會的折射,是生活的一面鏡子。《深圳我城》所展現的深圳城市變遷,脈絡清晰,軌跡明顯,既有形象感染力,又有思想感召力。它表明,“深圳奇跡”是深圳人敢闖敢試創造出來的,“深圳精神”是深圳文化創新的思想先導和精神結晶。作為一本報告文學集,《深圳我城》不僅讓我們領略到文學之美的審美感受,更使我們獲得觀照深圳、思考城市的思想啟迪。作者在有意無意間達到了“舉精神旗幟、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的境界和高度。令人敬佩,發人深思。
來源:《文化深圳》2022年第2-3期
作者:吳俊忠(深圳大學教授、深圳大學城市文化研究所原所長、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原理事)
(聲明:本網站轉載其他媒體內容,旨在傳遞更多信息及用于網絡分享,不具有任何商業目的。如有版權異議及其他任何問題,請與我們聯系,我們會盡快妥善處理。)
深圳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官網:http://www.1111567.com
郵箱:swlcyb@shenzhen.com.cn



